德国艺术史家施纳泽(carlSchnaase,1798-1875)早在1850年就骄傲地宣称“艺术史的知识已经完善,许多问题业已解决,艺术史的全景图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施纳泽如此雄夸之语,显然是建立在自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l-1574)、温克尔曼(Johan JoachinWinckelmann,1717-1768)、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Hegel,1770-1831)等以来艺术史研究的深厚传统之上。而与艺术有着共同渊源的设计,在瓦萨里开始将艺术纳入正式的历史研究的范围之中的时候,与艺术正式相分离,也因此未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虽然他所谓的艺术正是“设计的艺术”(Arti del disegno),却恰是以“设计”(disegno)为名,将今日所谓与设计相关的手工艺排除出艺术的范围。直至桑佩尔(Gottfried Semper,1803-1879)对工艺的重视、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i896)对小艺术(the lesser arts)的大力强调,并以艺术与工艺(arts and crafts)相并列,艺术与工艺(设计)才重又相聚,设计史的研究才借此而开始。以时间而论,如果从桑佩尔1860年至1863年期间出版的《工艺美术与建筑艺术的风格》(DerStil in den technischen undtektonischen K(insten)算起,也只不过140年左右,而如果从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1902-1983)1936年出版的《现代运动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佩斯》(Pioneers of Modern Mbvement;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Gropius)算起,则不满80年。设计史显然无法与艺术史研究的悠久传统相比,而只能说“许多问题都等待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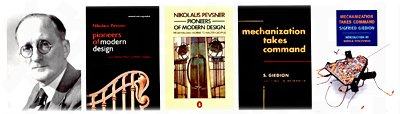
艺术与设计各自开展其历史研究的开始之处,正是其一分一合之时,这一有趣的事实上的历史关联,兆示出它们在历史研究上的密切关联。的确,从西方设计史的研究现状来看,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与结果对设计史有着直接的帮助,其影响痕迹十分明显。设计史的研究成果,一部分已然包括在艺术史之中,而设计史的研究方法,则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直承艺术史而来,一类以设计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前者加以补充甚或突破。前者包括瓦萨里开创的传记模式、沃尔夫林(Heiich Wolfflin,1864-1945)开创的形式分析方法、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等人的图像学方法;后者则包括桑佩尔从建筑史研究而来的“艺术材料主义”、李格尔(AloisRiegl,1858-1905)的图案分析、福蒂(Adrian Forty,1948-)的社会史研究、康威(Hazel Conway)等人的集体写作模式以及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所启迪出的类型学与时尚批评写作相结合的方法。
一、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因袭
维克多·马格林(VictorMargolin)在其《设计史在美国(1977-2000)》中写道:“艺术史对设计史学家有很大的帮助……当艺术史学家开始考虑设计时,他们往往按照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制定的那些得到现代艺术博物馆所推崇的现代主义规则。”马格林的这番话实际上包含着几个意思:其一,艺术史的确对设计史有很大的影响;其二,这种影响直接表现在艺术史家对设计的关注,艺术史家对设计的关注自然会提供出一个“艺术史式”的设计史研究模式。其三,这种模式其实已经体现在开设计史研究先河的佩夫斯纳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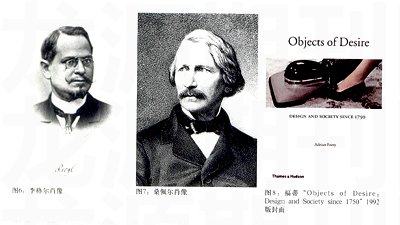
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研究,的确深受艺术史研究的影响。
首先,这种影响表现在对设计师个人的生平与成就的重视上。他在((现代运动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佩斯》中把莫里斯指认为“现代运动(ModernMovement)之父”,并认为“我们应该把下列成就归功于他,即一个普通人的住屋再度成为建筑师设计思想的有价值的对象,一把椅子或一个花瓶再度成为艺术家驰骋想象力的用武之地。”这种口吻,在瓦萨里的《意大利著名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生平》(Le Vite de" piu ecceilentiarchitetti, pittori, et scultoriitaliani, da Cimabue insino a"nostri Tempi)中不难找到,显然,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研究仍然是将瓦萨里所开创的艺术史传记模式的一个延伸。佩夫斯纳本人1924年从莱比锡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这一出身显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佩夫斯纳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建筑与装饰艺术,但他想以“设计”(1949年再版时将书名改为Pioneers of ModernDesign From William Morris toWalter Gropius)概念替换19世纪末还在使用的“大艺术”和“小艺术”概念,所以将研究内容扩展到“1890年的绘画艺术”(书中第三章),与瓦萨里相比,研究内容上的重叠(建筑、绘画),也使得研究方法上的因袭极为自然。换言之,佩夫斯纳把瓦萨里的艺术家换成了设计师,瓦萨里是记载乔托、马萨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这些艺术精英们的生平、艺术成就,而他是对莫里斯、范·德·维尔德、麦金托什、赖特、卢斯、贝伦斯、格罗佩斯等现代设计先驱们的“为世公认的业绩进行详细的论述”。
其次,这种影响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传统艺术史的研究,由于极为注重重要艺术家的个人成就,也就自然会选取其重要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在近代艺术体系以美术馆、博物馆为依托的情形下,美术馆、博物馆内的作品自然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正如马格林所指出的,佩夫斯纳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是如此。他所选取的设计作品,都是设计先驱们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也都是博物馆要加以收藏的经典作品。
如果说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研究方法是直接因袭古老的艺术史研究传记模式,即所谓的“精英方法”的影响,那么,吉迪恩(SigfriedGiedion,1888-1968)则受到了一种较新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形式分析法的影响。
吉迪恩以其《机械化指挥:对无名史的贡献》(MechanizationTakes Command: A Contributionto Anonymous History,
1948)声名远著。其研究方法与佩夫斯纳正好相反,佩夫斯纳重视有名望的设计先驱及其作品,而吉迪恩却重视无名
者,而强调“无名的技术史”与“个体的创造史”同等重要。他在书中所研究的个案,如芝加哥屠宰场的传送带、弹簧锁、柯尔特左轮手枪等等,显然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设计师与作品的选择上,吉迪恩都开辟了一个与佩夫斯纳不同的研究模式。其实,吉迪恩的“无名的技术史”研究,直接师承于其授业恩师沃尔夫林所倡导的风格分析与“无名的艺术史”。沃尔夫林在其名著((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Princilales of ArtHistory)中,提出了诸如线描与图绘、平面与纵深、封闭性与开放性、多样性与同一性、清晰性与模糊性等五对概念,倡导对艺术作品进行形式分析,强调艺术形式的独立品质。这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正与传统传记模式相区别。所以,实际上,吉迪恩与佩夫斯纳设计史研究方法的区别,是艺术史研究方法转变的一个延伸。
不过,虽然吉迪恩设计史研究的方法来自于老师沃尔夫林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但设计作品与艺术作品的差别,使吉迪恩不能够完全依照老师的形式分析法对独立的作品进行分析,而采用了类型学的方法。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史家可以分析单独一件作品,但设计作品往往是成批生产的一系列产品,因此,设计史家必须要对设计作品进行分类。吉迪恩因此走向了类型学,除了上文所列的屠宰场、弹簧锁、左轮手枪以外,还研究拖拉机、家具、浴室等等。正如夏洛特(Charlotte)与蒂姆·本顿(Tim Benton)所认为的,“建筑类型与风格之间往往会相互关联。”吉迪恩的类型学研究是从风格分析之中过渡而来。吉迪恩清楚地认识到:“一种时刻关注相互关系的、适应我们时代的问题处理方式,这就是类型学方法。风格史的主题是水平方向的,类型史则是垂直方向的(水平线等同于历时,垂直线等同于同步?)。如果要将事情放置在历史空间中审视,两者都是必须的。”显然,吉迪恩在直承沃尔夫林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修补。其后,佩夫斯纳在其《建筑类型的历史》History of BuildingTypes,1976)中也引入了类型学研究,研究了包括政府办公室、国家纪念碑、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医院、酒店、车站、商店和工厂等在内的20种类型的建筑。
在对类型学方法的运用上,吉迪恩与佩夫斯纳相同,但因为各自对不同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因袭,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仍然有着明显的分别。吉迪恩遵循沃尔夫林的方法,即使留心设计者,但并不关心其生平,而佩夫斯纳仍然重视著名的设计师及其著名的作品,但同是类型学研究,在对设计作品的分析上,他们都重点分析设计作品的社会功能。类型学的功能分析,其实又跟艺术史研究的图像学方法有着一定的关联。
潘诺夫斯基等人在艺术史研究领域所倡导的图像学研究,重视的是艺术作品的内容分析,如神话、历史、文学等。对于设计作品而言,一方面既可以视为图像,直接用图像学的方法来探寻其特定的含义,或者追寻其艺术史,设计史的传统,如某一装饰纹样的象征意义等;另一方面,设计作品的内容,就是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类型学对功能的分析,其实就是图像学的一个变体。
二、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补充与突破
吉迪恩以类型学方法代替老师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方法,表明设计史与艺术史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在方法上不可能完全一致。设计史自身的特点需要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做出一定的调整,甚或突破而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
作为设计史研究的先驱,桑佩尔以“艺术材料主义”(artisticmaterialism)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强调建筑、工艺美术的风格与环境、技术、材料、功能等因素之间的紧密关联。桑佩尔学习建筑多年,他对建筑受环境、技术、材料与功能的影响这一事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加之在思想上受达尔文的影响,自然十分强调外在的物质因素对设计发展的影响。他对建筑史的研究,是以实际行动在反对温克尔曼将建筑排除在艺术史之外的观念,并且在事实上将建筑史从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独立出来。他重视诸如陶制品、纺织品、金属制品、挂毯等工艺美术产品,将其与建筑相并列,从而提高了“小艺术”的地位,使其进入历史的视野。所以,桑佩尔对设计史研究的开拓,可以说是其建筑史研究的一个延伸,正因为沿用的是建筑史的研究方法,所以对功能、技术、材料、环境等外在因素极为重视,因此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相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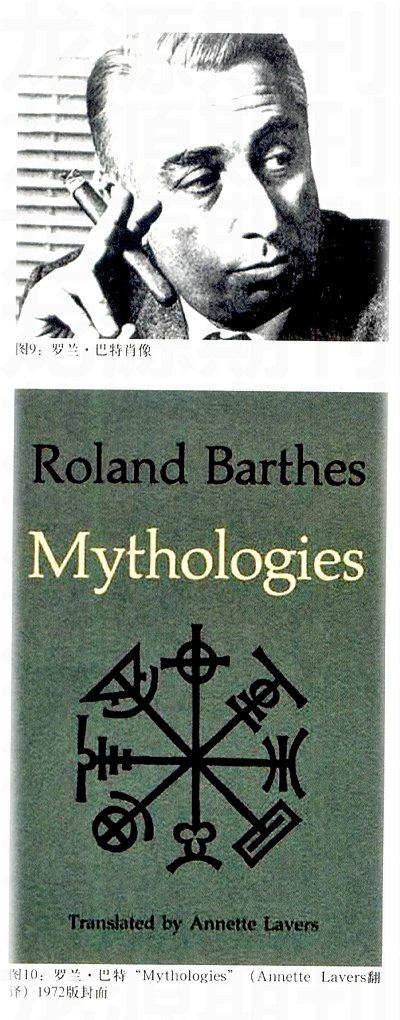
桑佩尔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其机械的一面,但却能够提醒研究者注意设计与技术、材料的关联,从而去挖掘设计史与科技史的关联。保罗·克拉克(PaulClark)与朱利安-弗里曼(Julian Freeman)所写的《设计:速成读本》(Design:A Crash Course)一书,就是将设计与科技相结合的一个极好的研究成果。而亨利·佩卓斯基(Hey Petroski)的《器具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Useful Things)则很难辨认是设计史还是科技史。
另一位设计史的先驱李格尔对设计史研究的开拓,表现于对装饰图案的重视。李格尔在奥地利艺术与工业博物馆工作,多年的博物馆工作使他对各种装饰图案十分熟悉。在《风格问题:装饰艺术的历史》(Stifragen,GrundlegungenZu einer Geschichte derOrnamentik,1893)一书中,李格尔对埃及莲花纹样、棕榈叶纹样、希腊良苕纹样以及阿拉伯纹样做了细致的研究。由于19世纪设计的中心是装饰,所以,李格尔的图案研究开辟了设计史研究的一种独特模式。李格尔反对以往艺术史所认为的艺术发展的循环理论,认为所有阶段的艺术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由此,他进而认为装饰艺术的历史从未间断,而是围绕几个母题在不断地变化与持续。真正的推动因素是来自于艺术内部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而不是桑佩尔所说的环境、技术、材料等外在因素,装饰艺术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跟外在因素关系不大。李格尔对桑佩尔的批评使设计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走向丰富,并提醒研究者关注设计史自身的内部规律。由于李格尔并无大艺术与小艺术相分的概念,所以,其研究方法应该说是艺术史与设计史共同的研究方法。
李格尔在其另一部设计史著作(《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Lafe Roman Art Industry)中所强调的以“知觉方式”观察艺术史(设计史)的“观者”理论,与后世兴起的接受美学走到了一起,共同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对接受者的关注。艺术史的研究,一直缺乏对类似“每一件艺术作品的收藏史”的研究,或者说缺乏对接受者的足够重视。而由于每一件设计作品都不得不直接面对接
受者,只有获得接受者的认可才算成功,换言之,接受者的需求与接受对设计而言至关重要,所以,设计史的研究无法回避接受者这个维度,因而也无法回避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且,相比而言,设计史明显比艺术史更为倚重对社会文化的研究。
福蒂的《欲望的对象:1750以来的设计与社会》(Objects of Desire:Design and Society since 1750)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典范之作。福蒂明确指出:“设计史就是社会史。”他批评英国的研究者将设计仅仅与眼睛相关联,而隔断与社会意识和钱袋的关联,把设计局限于艺术活动,使之显得无足轻重,也使之沦落为文化的附属品,从而严重低估了设计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工业财富的创造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设计与艺术的差别,关键在于艺术品通常成于一人之手,因此,艺术家往往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以至于可以自由表达创造与想象,但设计物与此不同,在资本社会里,不管设计在其中起何种作用,产品得以生产的首要目的都在于产生利润,而系列产品往往由一群设计师共同完成。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亨利·佩卓斯基对无名的改进者的尊重,福蒂既批评将设计的变化归因于艺术家或设计师个人的个性与生涯,也反对将人工制品视为动物和植物,从而把设计的变化归因于某种向完美形式进化的观念。福蒂一再强调设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设计的历史变化不是决定于其内在的基因结构,而在于其制作者、工业家以及他们与接受设计产品的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福蒂的社会史研究方法,既不同于吉迪恩与佩夫斯纳、也不同于桑佩尔与李格尔,更与艺术史所采用的社会史研究有着近似根本性的区别。
艺术史其实也重视与社会的关系研究,诸如瓦尔堡(AbyWarburg,1866-1929)、贡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1933--2008)及哈斯克尔(FrancisHaskell,1928-2000)等人所开展的艺术赞助的研究,就将艺术品的收藏与接受问题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诸如豪泽尔(Arnold Hauser)、威特金(Robert Witkin)等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艺术史的研究,将艺术纳入到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但艺术与社会的关联,或者止于与赞助人——非平民阶层,或者止于福蒂所批评的“社会情境”(socialcontext)或“社会背景”(socialbackground),而设计与社会的关联,则显然与此不同。如果说艺术与社会精英脱不开联系,而设计则在本质上是平民化的。作为“现代设计之父”的莫里斯曾说:“如果不是人人都能欣赏的艺术,那艺术跟我们有何相干?”在现代设计的开端之时,就已经期许设计的平民化而去其精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蒂的社会史研究才不同于艺术史的社会史研究,他认为所谓的“社会情境”或“社会背景”是一种极为“草率的”(cursory)参照,应用到设计史研究领域,则是特别“糟糕的“(deplorable)。
但如何开展社会史研究呢?福蒂极有信心地认为可以借鉴结构主义的理论。他推崇罗兰·巴特的(《神话))(Mythologies,1957),认为设计具有实现神话并将其变为持久的、坚实的、可触摸的形式的能力,比如通过广告、新闻、电视等手段将神话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以现代化的设备,使办公工作变得有趣、舒适、兴奋。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使设计史真正与社会史融为一体。不过,可以想见,这样的研究方法,难度极大,福蒂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设计广泛的影响与复杂的性质不能做简单的历史处理。同时,他还发现,设计产品的数量无限,要展开历史的研究,除了要极为慎重以外,还不得不追踪产品类型,像吉迪恩、佩夫斯纳一样,直接面对设计类型。他最终也走入了类型学研究。
当然,福蒂是带着社会史的眼光来进行类型学研究。当他在研究中指出设计产品数量无限,并强调设计产品往往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之时,他的类型学研究其实预示着另外一种设计史集体写作的研究方法。的确,设计的类型太过广泛,一人之力有限,集体研究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康威的《设计史:学生手册》(Design History:AStudyent’s Handbook)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
亨利·佩卓斯基的(《器具的进化》显然受到了福蒂的影响。当然,他所采用的研究方式,也明显受到了吉迪恩“无名的技术史”的影响。他所选择的一些器具类型,如回形针、拉链等,都是在接受与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的,有的发明者与改进者留下了姓名,但更多的产品“是由不知名的人士完成的”,“是成千上万个无名专业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绝不是一个设计者或工程师独立完成的”。这正是设计与艺术最大的差别。福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追问器具为何得以持续进化的过程中,福蒂的影响再次表现出来。佩卓斯基从功用的角度看产品的流传,将器具的进化放在设计者、工业家、使用者等与之相关的社会群体之中时,经济、政治、流行、环保、需求与欲望等各种因素都成为推手,正是福蒂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典型的延伸。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器具的进化》可以视为产品的接受史研究。走在他前面的是赫布里奇(D.Hebdige)的((作为形象的物品:意大利的踏板摩托车》(Object asimage:the Italian scooteF cycle,1981)。赫布里奇的论文关注意大利设计的踏板摩托车在英国的接受情况,有趣的是,其中还涉及广告、电影和旅游业中关于踏板车的描述,因此把设计与时尚联系在一起。
福蒂在推介巴特之时强调代替传统神话载体的电影、广告、新闻写作、电视等媒介,实际上也是在展示设计与时尚的关联。这种关联性的研究,在巴特的《神话》、《流行体系》(Systeme de la mode,1967)中早已被开拓出来。巴特以符号学的方法分析了其时的一些时尚产品,尤其在《流行体系》中依据两本法国时尚杂志进行分析,虽然他并没有将历史研究纳入其中,但他对时尚的评论,却直接刺激着设计史研究将类型学与时尚批评写作相结合的方式的出现。作为佩夫斯纳学生的班汉姆(Peter Reyner Banham,1922-1988)在以((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Theory and Designin the First Machine Age)获得博士学位以后,1958-1965年期间曾为英国流行杂志Statesman撰写专栏文章,论题包括超短裙、太阳镜、家用小装置等等,以其设计史的眼光来审视流行文化,提供出了一种新的研究与写作模式。与之同时,美国小说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开创了报道式写作,并将其运用到对设计产品的批评之中,从1965年的《糖果色柑橘片流线型小亲亲》(Tht Kandy-coloredTangerine-FlaKe StreamlineBaby,1965)到1981年的《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屋》(From Bauhaus toOur House,1981),设计批评的内容从加州小男孩设计和改装的汽车到建筑,以俚语、广告词、方言夹杂其中,对美国的时尚文化加以描述与分析。班汉姆与沃尔夫以设计批评的方式,对各种类型的流行产品加以探讨,注重其风格的社会意义,为设计史提供了一种将类型学与时尚写作相联系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在消费文化不断深入、时尚产品快速更新换代、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正方兴未艾,有着广阔的前景。
综合起来看,福蒂的研究代表着对设计史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所引发的,将是一种更为开放的设计史研究,将社会史、结构主义、人类学、符号学、类型学、图像学、材料学、接受美学、时尚批评、女性主义(如JudyAttfield用女性视角来检视设计史)等等融为一体,从而对设计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做出更为清晰的分析与阐明。(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邵宏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