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称红军时期。其间,任弼时先后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委员会成员、中央代表团成员、苏区中央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红六军团随军中央代表及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方面军政委兼二军(原红二军团)政委等职,参与领导、指挥党的军事工作与行动,从而对红军的创建作出了许多贡献。他的贡献不仅推动了红军的发展与强大,而且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经验,影响深远。
参与规划和指导党的军事工作,为红军立下“家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力扛起中国革命重担,开启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新阶段。创建工农军队、制定军队作战方针等军事问题,迅速占据重要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弼时受命在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期间,和李维汉、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而投身于规划与指导党的军事工作。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留守)发出了《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通知。这个重要的军事文件,是任弼时以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改写而成的。

《大纲》适应“对于军事问题现在急于需要一个整个的规划与指导”的现实,首先提出了以后的军事运动应遵守的原则,即工农群众的军事化,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以及注意与敌人战斗时的战术。
《大纲》指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为使红军基础稳固,“红军须有广大之工农分子参加,先选把(拔)赤卫队中勇敢分子,尤其是同志加入红军”。“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红军兵士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为此,“利用红军兵士集中施行政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可使红军兵士的政治认识与宣传组织工作能力增高,而且在退伍之后,乃至偶尔失败之时,均能使他们回到乡村成为群众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这样的立意,真可谓深谋远虑、百年大计。
在党和红军的关系方面,《大纲》规定:党的军事(委)必须成为健全而有力的组织,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同时即为党的军委”。“政治委员应即为党的代表”,他负有监督军官和进行政治工作之责。“红军之调遣,须服从割据区域苏维埃之命令。”红军党的组织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分支部。鉴于红军战斗多以连为单位,故“每连人数为较多时,得暂以连为单位,设立支部”。这些规定,突显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且有了支部建在连上的设想。
《大纲》对红军生活的规定体现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如“红军的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一切礼节,只以表示亲爱与整齐为主”。对红军经费的管理,“应设立经理委员会,兵士选举代表参加”。
历史表明,这份中共最早的《军事工作大纲》所规定的重大原则,如重视工农武装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要抓牢政治教育,保持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实行内部民主;支部可以建在连上;战士要能打仗,还要能做宣传工作等,对一年多后产生的“九月来信”(《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及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有着直接且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三者一脉相承,又表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发展与完善上。因此,说《大纲》的各项规定为后来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初步基础,也毫不为过。
6月5日,临时中央常委会(留守)通过了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长信,批准红四军以江西永新为中心深入开展工作,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创建湘赣两省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为保证计划的顺利执行,长信特别指示: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前委所管轄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前委受所在地省委指导,同时与湘赣两省省委发生密切关系。中央关于组织红四军前委的决定,以及对前委不受地方党部指挥的授权,深得红四军高层的赞赏,“认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因为像红四军这种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地方县委与特委的指挥,也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否则,就不免为地方主义所拖累。红四军此前在湖南及湘赣边界,多次在地方主义指挥下失败的教训,从反面证明:“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下,才能适应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毒害。”由此可见,中央这封长信在红军的实际斗争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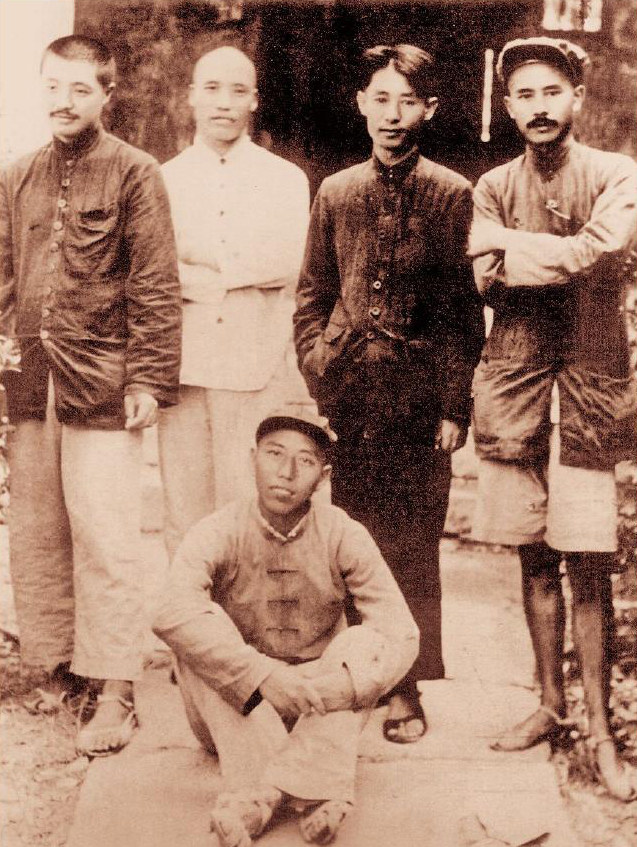
同一天,任弼时草拟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信,指示“要在此时加紧派人到赣南各县工作”,“是为至要”。同时要省委设立专门接头处,“接受前委的交通”,使前委与省委及中央的联系“永不中断”。显然,这封信是为落实前述中央给朱毛并前委长信指示精神而写的,足见任弼时(当然也有中央留守班子)虑事之细、行动之快。
7月,中共中央(留守)发出任弼时起草的关于《兵运策略》的第58号通告。通告针对国民党打下平津后,各派新军阀开始“裁兵”和肃清内部,引发军心动荡、兵变不断的现实,指出各地党组织目前“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通告对敌军士兵的社会成分及其地位作了详细分析,告诫各地:应从积极方面去看待士兵工作,要利用敌人征兵、下级军校招生时,多派工农分子进去,借以造成红军的另一种来源。
综上所述可知,任弼时参与制定的《军事工作大纲》《兵运策略》,以及《城市农村工作指南》通告中所规定的农村游击队建设的分散性、普遍性、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等,体现了中共中央有关红军建设的基本思想,是对红军立下的“家规”“家训”。不论在当年,还是在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都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乃至决定性影响。
注重“两条腿”走路去产生、壮大红军队伍,给红军广开兵源
1944年10月26日,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说:“一般地说,红军的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旧军队暴动过来改编为红军的;一种是从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为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集合而为红军的。”任弼时的这个总结,其实根源于前述《军事工作大纲》和《兵运策略》,当然还有此后他的实践与体会。
当中国革命进入以土地革命战争为主要内容与形式的历史新阶段后,为红军源源不断输送兵源,不断扩大红军队伍,就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弼时深知其义,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工作,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并以“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即一方面通过兵运工作,去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反正,拖抢过来当红军;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动员、组织工农群众实行军事化,由赤卫队(或少先队)而到补充师(团),再到正规部队当红军。
1928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在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留守)几次会议时,一再提及要“利用国民党军阀借口裁兵排斥异己之机,注意士兵运动”;安徽省临委在军事工作方面不要沉溺于“土匪”工作,而要注意士兵运动;满洲省委在奉军出关后士兵更痛苦之际,“应设法在敌军中发展党组织”;批评广东省委对待士兵运动态度消极,对白军士兵的认识片面乃至错误。9月12日,他受命起草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责成广东省委取消兵运决议案,“完全根据中央的通知,去进行一切工作”。他还提醒江西省委注意,驻江西的敌二十九师(贵州兵)无饷,兵士无出路,我方已派人去做工作,届时设法联系、接应。
相较于通过兵运为红军争取兵源,任弼时更多地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的工作上。这完全符合割据区(后之苏区)实际:一则割据区工农群众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且有跟共产党闹革命的愿望;二则红军既是为工农谋利益的武装集团,工农群众必然拥护而积极投身之。要使这个可能变成现实,还须有适当的动员组织和政策措施。
1931年4月4日,任弼时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到达江西瑞金,开始了在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长达三年多的生活。置身苏区,他对加强红军建设有了更为直接而深切的体会,对开展扩大红军运动有了更多的办法。
 主任、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委员、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任弼时讲团结不是搞一团和气,而是着眼于思想认识上的一致,从斗争中求团结。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即考虑如何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从思想上以“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为基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在他的教育引导下,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等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转而支持北上方针。
主任、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委员、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任弼时讲团结不是搞一团和气,而是着眼于思想认识上的一致,从斗争中求团结。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即考虑如何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从思想上以“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为基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在他的教育引导下,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等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转而支持北上方针。工作上,任弼时坚持集体领导,凡是重要的问题,大都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即便情况紧张,也尽可能集体讨论,或由主要负责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讨论问题之前,他总是多方搜集材料和各人意见。讨论问题时,他又很注意倾听别人意见,不先表态、作结论。事情一经集体讨论决定后,大家都得照办,绝不允许会上一套会下一套。所以,任弼时领导过的不同班子,都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例如,1936年8月上旬,中共西北局要在包座河西畔的求吉寺开会。会前,任弼时同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多次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会上,他要大家紧紧团结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引导大家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上来,而不必纠缠于以前的问题。这样做,使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
反对并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维护了党的团结、红军的团结
1936年6月初,红六军团第十六师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会合时,张国焘派出的“工作团”应任弼时要求,送来一批包括《干部必读》在内的文件和材料,其中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之后,任弼时、贺龙等在和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来人的谈话中,也听到类似言论。任弼时对此事作了果断处置:一是赞同王震下令把文件材料烧掉;二是告诉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指示保留一份,余皆烧掉)。可以说,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跟受到任弼时他们的坚决抵制,有很大关系。
7月初,张国焘与任弼时面谈时提出:“六军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都遭到任弼时拒绝。此后,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提出召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的干部会,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任弼时告诫来人,唯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并反对召开上述会议,指出,如果“造成上面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当张国焘再度提出召开联席会时,任弼时愤然说:如果红二、红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不能以多数(红四方面军人多)压少数。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内部,张国焘和任弼时的争论日益严重。张国焘口头上赞成,实际上反对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在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上,主张一是往西,二是出东南。任弼时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张国焘的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懂得如何估量当前形势下阶级力量的变动。在任弼时行将返回红二方面军前的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跟朱德诚恳奉劝张国焘不要怕北上和党中央见面,错了就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不再搞派别活动就不会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由此可见,任弼时对张国焘的斗争真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既坚持原则,又不乏革命灵活性。
以上所述仅是任弼时对红军创建的部分贡献,但它已足以成为任弼时在人民军队创建史上的一座丰碑。


